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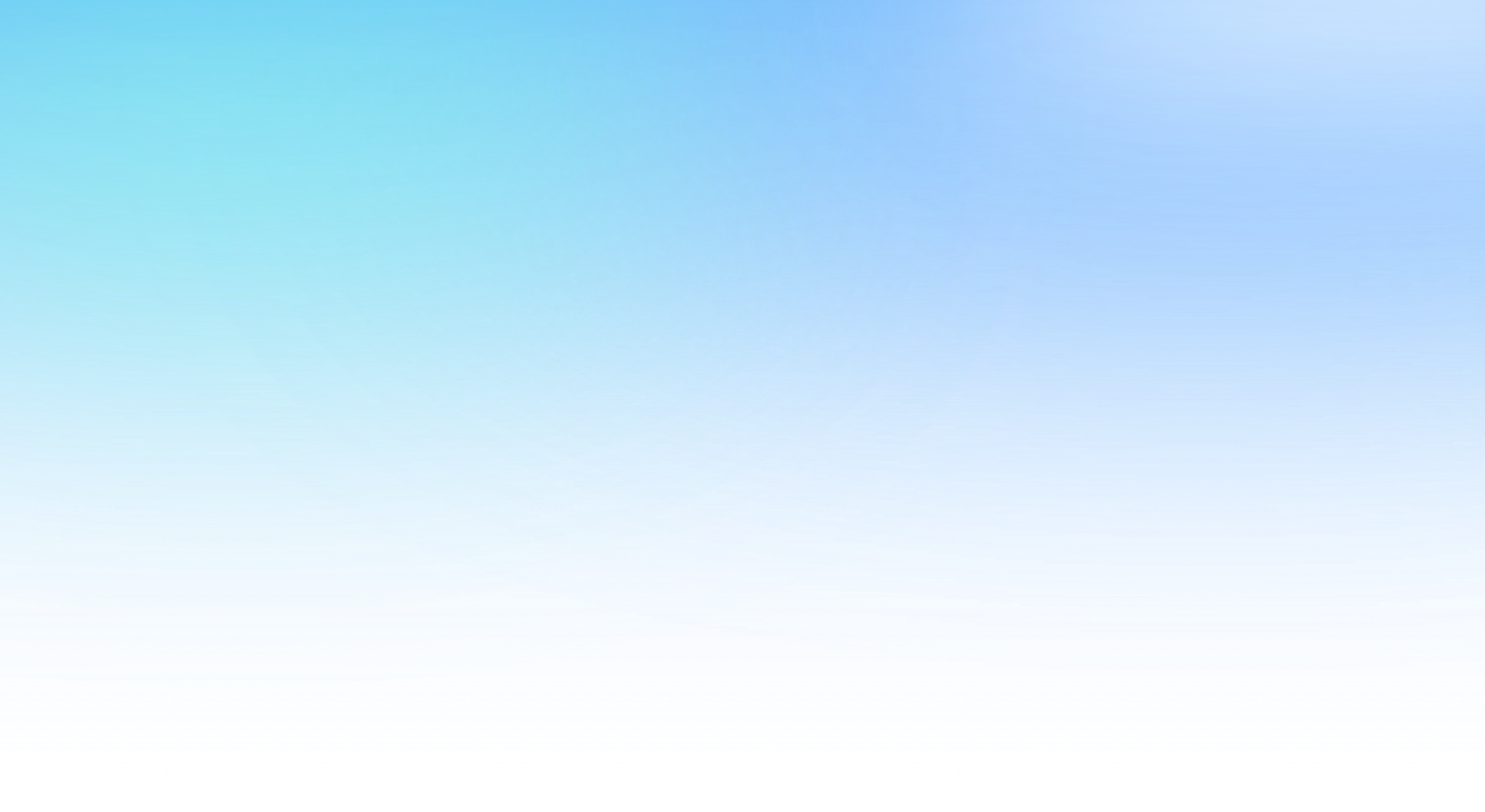

“陈医生,我妈又不肯吃药了,你能不能来一趟?”国庆节前一天的晚上8点过,西区格里坪镇卫生院的陈肇芳医生回到家刚端起饭碗,手机铃声响了,对方焦急的话语让她不得不放下碗筷出门去看病人。像这样的突发状况,在她做家庭医生的十年里,早已成为寻常事。
谈起十年前刚做家庭医生的情景,陈肇芳说:“碰过的‘钉子’能装满一箩筐。”

到村卫生室为村民看病
那些境遇让她记忆深刻——揣着签约表上门,迎接她的常常是“砰”的关门声,或是隔着防盗门的冷言:“是不是来推销保健品的?”“社区医院能看啥病,不就开点感冒药吗?”她攥着被拒了几十次的表格,常对着空荡的楼道发呆:什么时候,他们才会信任我?

入户看病人
“家庭医生的工作这么难开展,你怎么坚持下来的?”
“医者仁心,好事多磨嘛。”陈肇芳回答记者时笑得很灿烂。
5年前,80多岁的李阿姨身患糖尿病、高血压等,子女在外地。她第一次上门随访,经检测,老人的血糖比正常人血糖高出很多,已经接近危急值了。老人却自顾自吃着蜜饯:“活到这岁数,吃口喜欢的还不行?”
陈肇芳没有直接制止,而是坐下听老人讲往事,讲自己如何从东北虎妞成为三线建设的一员,又在攀枝花市扎了根。讲到最后,老人眼里泛起了泪光:“医生,我不是不想活,只是太孤单。”
从那以后,陈肇芳总绕路去李阿姨家,有时是帮她测血糖;有时就坐着听她唠嗑,顺手把藏在厨房吊柜第二格的蜜饯罐悄悄挪到她够不着的冰箱顶层。“看不见就少吃点。”陈肇芳笑着提醒。李阿姨也不恼,掏出小本本认真记着血糖值。
后来,李阿姨逢人就说:“陈医生比我闺女还懂我家事!”

到村民家为老人检查
“做家庭医生时间长了,渐渐地就会与病人间有了亲情。”陈肇芳笑着说起与田大娘家的一件事。
去年,田大娘去外地旅游时,她自理能力较差的女儿突然急病发作。当天陈肇芳不值夜班,接到电话后她一边联系社区工作人员送诊,一边揣着钱包往医院跑,垫付3000元医药费帮助病人办理了住院手续。
一周后,田大娘带着锦旗找到陈肇芳,锦旗上“情系患者,服务一流”八个字格外醒目。田大娘握着她的手反复道谢,可她总觉得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。
“当然,这条路也不全是暖光。”陈肇芳说,她曾为慢性病患者老周调整两个月的降压药方案,眼看着他血压稳了,他却突然要解约——“私立医院送免费鸡蛋,比你这里划算。”还有一次,她被患者家属堵在候诊区骂:“你们就是想赚我们的钱。”声音大得整个大厅一下子都安静了,所有人的目光看着她,她攥着病历本的手,指尖泛了白。
最惊险的那次,陈肇芳至今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小李拒绝服药,他的母亲偷偷给她打了求助电话。她刚踏进李家院门,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就朝她劈来。“我没病,我不去住院。”小李眼睛赤红,嘶吼声震得人耳朵疼。她脑子里一片空白,只知道转身往院门外跑。直到反锁上大铁门,她靠着冰冷的铁栏杆,才发现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。
等小李情绪稍稳,她还是立即联系了专科医院,陪着病人的家属跑前跑后办转诊。同事后来问她怕不怕,她说:“怕啊,可他是病人,我是医生,总不能看着他的病情发展得更严重。”
那天傍晚,小李的母亲特意来告诉她:“陈医生,谢谢你没放弃我儿子,他的病情现在好多了。”那一刻,她的泪水模糊了双眼。她忽然明白,支撑她走下去的,从来不是锦旗和感谢,而是患者重获健康的笑容,是家属卸下重担的轻松,是那句“陈医生,我们信你”。

入户随访
十年“家庭医生路”,陈肇芳只有测不完的血压、调不完的药量、深夜里响不停的咨询电话等。但就是这些琐碎的日常,让她慢慢走进了居民的心里——李阿姨会把刚煮好的玉米塞给她,田大娘总记得她爱吃香菜,就连曾经骂过她的病人家属后来也会主动跟她打招呼。
“如今,在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很多像陈肇芳医生这样的家庭医生,以仁心守护万家健康,用脚步丈量医患真情。”西区卫生健康局有关负责人说,目前全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稳步提升,重点人群签约率已超90%。
该负责人表示,西区将持续深化家庭医生服务内涵,优化签约服务模式,努力提升服务质量与可及性,真正让家庭医生成为居民身边的“健康守门人”,筑牢健康守护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