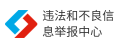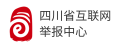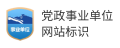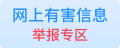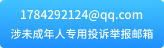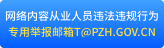默认栏目
时代、城市、工业:攀枝花文学的别样图景
 0
0
编者按:
“文学攀军”在四川文学版图上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,也是攀西文学的一道靓丽风景。伴随着攀枝花六十年如歌岁月的洗礼,“文学攀军”也经历着阵痛、演变、涅槃的艰难历程。如今,异军突起的“文学攀军”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创作上,均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。近日,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的《四川作家》于2025年第6期,以专访的形式对“文学攀军”现象进行了深度报道,现予摘编转发,以此激励“文学攀军”创作出更多有温度、有力度、有高度、有辨识度的文学作品。
时代、城市、工业:攀枝花文学的别样图景
《四川作家》:攀枝花文学的发展与城市建设的历程密切相关。20世纪60年代,随着三线建设的推进,攀枝花逐渐成为工业重镇,文学创作也开始萌芽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时代浪潮之下的工业发展及城市化的进程也在迅猛加快,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请向我们梳理下攀枝花文学的历史发展。
攀枝花市作协:要梳理攀枝花文学的历史发展,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攀枝花这座城市的历史脉络。自1965年建市至今,攀枝花整整走过了60年的不平凡历程。攀枝花位于中国西南川滇交界部,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崛起的城市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没有三线建设,就没有攀枝花,自然也就没有攀枝花文学。同时它也是“四川南向门户”上的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贸物资集散地,是我国西部最大的移民城市。丰富的钒钛磁铁矿、灿烂的亚热带风光和独特的移民文化,熔铸了攀枝花独特的文学基因。这就意味着攀枝花文学是多元的、包容的、立体的。
攀枝花文学的历史发展轨迹,可从两个时间段来概述。第一个时间段为1965年至1994年:在这30年间,攀枝花文学经历了从无到有、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。1994年攀枝花建市30周年之际,攀枝花市文联、攀枝花市作协编选的大型“文学丛书”《攀枝花建市30周年文学作品精选》(五卷本)正式出版,共收录70名攀枝花作者的333篇(首)文学作品,主要包括短篇小说卷《太阳山谷》(48篇),中篇小说卷《难忘这条路》(8篇),散文卷《三月,与你同行》(94篇),诗歌卷《五琴弦》(167首),报告文学卷《攀枝花钢城赋》(16篇),共计120万字。这30年,伴随攀枝花开发建设的如歌岁月,一批40后、50后、60后攀枝花作家的作品相继出版或发表在重要文学报刊,并斩获省级文学奖项。刘成东的诗歌《格里拉山脊》《另一种超越》《给女儿》分别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十月》发表;陈元丁的短篇小说《蓝光鸟》、张和胜的小说《山谷梦》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;沙马的组诗《渴望》《回想家园》分别在《中国作家》《星星·诗刊》发表。任正平的短篇小说《第八颗上智齿》荣获首届四川文学奖,周强的短篇小说《在路上》荣获冶金部“铁流文学”一等奖,吕文秀的诗歌《僧寺》荣获河南省作协《大河诗刊》优秀作品奖。
第二个时间段为1995年至今:这30年的文学创作,完全可用“人才辈出,成就斐然”来概括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攀枝花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,由单一的“大工业”转型为现在的钒钛产业基地、康养胜地和全国共同富裕试验区,经历了由“阵痛”“抉择”到“重生”的过程。攀枝花的作家,既是这场“变革”的参与者,也是书写者。可圈可点的获奖作品有:沙马的诗集《梦中的橄榄树》荣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;刘成东的诗集《体验》荣获第三届四川文学奖;召唤的长篇小说《黑丧鼓》荣获第八届四川文学奖;沙马的组诗《南高原,幻影之伤》荣获第四届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;普光泉的长篇小说《一个说纳西话的人》荣获第五届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;钟少曦的长篇小说《金花塘》荣获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“北方八省二市”优秀图书评选一等奖;王子俊的组诗《山中隐》荣获第八届“扬子江诗歌奖”。
在《人民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四川文学》《诗刊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等重点文学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的作者,可用代际罗列,如40后的王俊超、赖俊熙、刘成东、吕文秀等;50后的沈国凡、钟少曦、张和胜、石宝霞、徐甲子、孙其安等;60后的沙马、周强、普光泉、召唤、黄薇、王子俊、陈元丁、马飚、杨荞宁、王幸、田青霞、王玉军、张良、董文军、刘成渝等;70后的李吉顺、曾蒙、温馨等。
2008年以来,我们在全省率先实施优秀文学创作人才引进、攀枝花文学院签约作家聘用制等举措,使得攀枝花文学创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。如召唤的中篇小说《芦花白,芦花飞》、短篇小说《半个月亮》分别被《小说选刊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转载;如黄薇的长篇散文《县联社》荣登2023年四川文学作品影响力排行榜,刷新了攀枝花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纪录。
在四川省作协年度重点作品扶持中,攀枝花作家也取得了不俗成绩。如李吉顺的长篇小说《安宁秋水》,召唤的中篇小说《牛轭湾》,温馨的诗集《采石场》,邓明莉的儿童文学《思无邪》,王玉军的长篇小说《井巷壁画》,黄薇的长篇散文《县联社》,召唤的散文集《麦浪漾起的村庄》,普光泉的长篇小说《白》等8部作品先后入选。马飚的诗集《太阳铁》入选2019年度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。
60年砥砺前行,如今的“文学攀军”基本构成了“四个方阵”的文学创作格局:一是以召唤为领军的“小说创作方阵”;二是以沙马为领军的“诗歌创作方阵”;三是以黄薇为领军的“散文创作方阵”;四是以普光泉为领军的“非虚构文学方阵”。
《四川作家》:攀枝花作为一座工业城市,攀枝花文学在工业题材的创作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工业题材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类型,在记录现代化进程的史册中,不仅承载着国家工业发展的集体记忆,也镌刻出了一代劳动者的成就与荣光。请问攀枝花文学在工业题材书写方面,有哪些重要作品?怎么看待工业题材的书写?
攀枝花市作协:在攀枝花60年的城市发展进程中,一直“在钢铁中生活”的作家们见证、参与并书写了这座“百里钢城”的“集体记忆”,在省级、国家级文学报刊发表(出版)的工业题材文学作品数以千部(首):长篇小说有钟少曦的《裂谷燃情》,李吉顺的《青春度》,黄文进的《东方寓言》,石宝霞的《空谷》,王玉军的《煤矿干部》《井巷壁画》等;短篇小说有张和胜的《山谷梦》,周强的《利好消息》等;诗集有刘成东的《体验》,王俊超的《钢花·诗花·攀枝花》,普光泉的《身体》《我在攀枝花》,黄薇的诗集《水边书》,马飚的《太阳诗篇》《太阳谷》,温馨的《采石场》等;散文有黄薇的散文集《梦着的蝴蝶》和散文《在钢铁中生活》;报告文学有沈国凡的《中国西部热土上的移民城》,普光泉的《攀枝花1965》等。
工业题材的书写,无疑要聚焦工业生产体系与工人群体生活,它不仅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文学镜像,更是广大工人精神世界的诗意呈现。与其他题材的文学书写相比,工业题材似乎不大“讨巧”,但蒋子龙的《乔厂长上任记》,张洁的《沉重的翅膀》这两部工业题材小说,丝毫不影响载入中国文学史。落脚到攀枝花这座工业城市,要想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工业题材作品,攀枝花作家除了用一腔柔情“捂热”那些“冰冷”的钢铁、煤矿、高炉、机械外,还得具备向经典致敬、看齐的自觉、自省意识,和大国工匠的“探险”精神。唯有这样,才能创作出别具一格的具有大气象、大格局的工业题材作品。
《四川作家》:目前,攀枝花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。文学创作要承担起时代使命,深入地挖掘、展现新时代的内涵与精神。文学工作如何抓住机遇、迎接挑战,推动文学创作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,以及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?
攀枝花市作协:攀枝花是唯一被列入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的地级市,这既是机遇,更是挑战。攀枝花文学也同样面临着高质量推进、发展、提升的课题,这就需要我们每位作家走出写作的舒适区,用敢于“吃螃蟹”的“探险”精神,深入到攀枝花“转型升级”的细微处,与时代同频共振,用独特的审美去洞察幽微的人性,超拔地书写有高度、有厚度、有温度的文学作品。
《四川作家》:书写反映时代变革的文学作品,既要展示出时代波澜壮阔的一面,也要通过刻画个体细微的生活来展现出普通人的筋骨与血肉。请谈一谈当前语境下,个体记忆、经验与时代视野、历史谱系之间的关系。
攀枝花市作协:所谓个体记忆和个体经验,其实都是“自我”“小我”在时代变革中的一个缩影,换句话说,“个体”的记忆也好、经验也罢,都是时代视野和历史谱系中的一个“符号”,有着独特的“个体性”和“差异性”。书写反映时代变革、展现普通人的筋骨与血肉的作品,作家仅仅凭着自己的个体记忆和经验是永远不够的。这就需要作家自觉地打破“自我”壁垒,跳出“小我”定式,去用纯粹、高洁、诗性的笔触,观照芸芸众生和大千世界。
《四川作家》:近年来,除了工业题材,攀枝花文学在乡村振兴、生态保护等主题方面,也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新时代精神的作品。请向我们介绍下这些作品。
攀枝花市作协:李吉顺的长篇小说《安宁秋水》,召唤的中短篇小说《牛轭湾》《羊在山上叫唤》、散文集《麦浪漾起的村庄》,张良的短篇小说《寻夫》,张龙的短篇小说《山那边》等作品,都以别致的叙述方式和审美形态,书写了攀枝花的乡村振兴和生态保护。
《四川作家》:《攀枝花文学》作为本土文学的重要阵地,为作家的成长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。在栏目设置方面也别出心裁,有“头条作家”“本土新秀”等重要栏目。请问在扶持新人新作和出作品、出人才方面,都有哪些重要的举措?
攀枝花市作协:《攀枝花文学》是由当年的《攀枝花文艺》《攀枝花》演变而来的,已有53年的历史。文学鼎盛时期的80年代,《攀枝花文学》面向全国公开发行,著名作家梁晓声、流沙河等都在本刊发表过作品。
在“文学攀军”版图中,诗歌创作是“重镇”,散文作品多如牛毛,而小说创作一直是“短板”。为了撬动小说创作这块“僵土”,自2021年《攀枝花文学》第5期始,就开始调整编辑方案,以“原创小说”“创作谈”“编辑札记”“作者简介”“作者生活照”的“捆绑”方式,在“特别推荐”栏目,首推了张亮的小说《散发香气的公路》。2023年,“特别推荐”栏目改为“头条作家”,用了整整三年(共18期)的时间,先后推出了攀枝花18位作者的短篇小说。其中,在《攀枝花文学》首发的张亮的《散发香气的公路》,张良的《寻夫》,普光泉的《我是药》,张龙的《山那边》等四篇小说,先后又在《四川文学》《红岩》《莲池》等刊发表。通过这一举措,攀枝花的小说创作队伍,得到了质的提升。
“本土新秀”栏目主要是发现和培养攀枝花籍的文学新秀。如陈可、周小童、庄吉等00后新秀,都是在读大学生。
《四川作家》:请谈一谈攀枝花下一步的文学工作计划。
攀枝花市作协:放在四川文学层面上来说,把“文学攀军”与兄弟地市州相比,还有很大的差距,单说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和四川文学奖两个奖项,除沙马获得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,召唤获得第八届四川文学奖外,十多年过去了,这两个奖项仍处于空白。
下一步,我们将以“一个中心”“两个突破”“三个着力点”“四个提升”来开展作协工作。“一个中心”即以持续打造“文学攀军”为中心。“两个突破”即在工业题材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上有所突破;在“大诗歌”和“大散文”创作上有所突破。“三个着力点”即着力完善文学人才培养机制;着力优化文学创作激励环境;着力转变文学创新思维模式。“四个提升”即不断提升“小说方阵”的影响力;不断提升“诗歌方阵”的冲击力;不断提升“散文方阵”的整体实力;不断提升“非虚构方阵”的辐射力。


分享至: